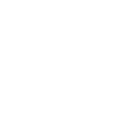不会老去
不会老去
叶红艳
当黑夜慢慢织上天空,窗前两棵高耸入云的老白杨树撑入云端,笔直而高长的树干上开出手掌般的枝桠,光秃秃的枝干上爬满了皱纹般的皮。火红的夕阳在它那陈旧皱巴的树皮上流动又跳跃,照出一片光晕开来。是的,时间便是如此一天一天从我们手指间流去的。我是见过不少夕日的,而此时忽忆起看日落的事,我突然想起外婆,想起许多过往的事。
我的大半童年时光是在乡下的外婆家里度过的。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外婆家门前栽种的两棵香樟树,同老白杨一般,也是高耸而望不到顶的。他的枝干强壮有力,树干虽高耸而却枝叶繁茂,散发青春的活力。而每当那一轮夕阳沉入山脉,这一天最后的光日一缕一缕的透过枝叶,那金黄色的光影斑斑点点投映在地,如此一钱,如此一两,陈酿着岁月与时光。
外婆应当是要这时候回来,她每日都在这个时候回来。我也总是习惯蹲守在门前,数着地上的树影,等着我的外婆回来。
我眼睹着这夕阳一点一点落下,这时,余晖是黑夜与白天最后的分界。那大抵是我最早地触碰时间。我擎着手指,横放眼前,手指上方,是寥落暗淡星辰的初夜,下方则是这一天里最后的一抹赤红的白昼,我努力地撑住手指不放开,想要拖住余晖,维持仅剩不多的白天。于是我每次都等来了,等来了路坡下的人影在跌跌撞撞地朝我走来,她隐约在向我招手。那时的我便觉得外婆的每次准时到家,都应该有着我不小的功劳。
每天天还没亮,外婆就会起早,不紧不忙的烧开一大锅油,旁边摆放着两大簸箕,簸箕上规整地陈放着清晨刚拣好的豆腐。油锅滚烫,豆腐白嫩,外婆使着长筷,来去自如地在油锅里翻转,一块块豆腐从清晨的石磨子里辗转而出,流落至如今的油锅里沉浮翻转,它的一生很短,但这就是它的一生。外婆炸的豆腐是村子里最好的,金黄酥脆的外壳,包裹着依旧白嫩入初的豆腐,一口下去溢出的汁水色香味甜,新鲜炸制好的豆腐上洋洒一层盐粒,保证口感的同时还能方便储藏。
每天,外婆装好豆腐,摆在三轮车上,寻着清晨的微光,蹬起三轮车,一溜烟便出去了。到了集市,便稳稳当当的停好车,清澈嘹亮的叫卖声唤醒了新一天的第一缕阳光,那时在我眼里,外婆仿佛永远年轻,不会倒下。
香樟树的花陆陆续续开了两三回,我也总归到了上学的年纪,于是便跟着父母亲去了城里念书,自此再也难见外婆了。
外婆是念佛的,每逢过年过节,都要去当地的寺庙里烧两大袋钱纸,红烛香火一大把一大把的买。而每逢五六月时,更是要千里迢迢地前往南岳山上进贡香火,求神拜佛。外婆总是说,只要我们这一家今年能够平安健康便是菩萨显灵了。而在我看来,这仿佛像是一种无意义的偏执,但是这话是不能单独说给外婆听的,是会挨骂的。
外婆生性直爽,脾气执拗。她帮我教训村里爱欺负我的孩子,教他们向我道歉,自此往后,那些孩子从此经过我们家,都只敢远远绕路走。也是这一年,外公挖坏了隔壁亲戚家的旧水管道,外婆赶忙让舅舅上门去赔礼道歉,平补是非。谁知那家人在牌局上谈起这件事竟口无遮拦,说起那管道新换不久,赔礼太少。于是人言亦言,三人成虎,这风言风语不久就传到外婆耳朵边。她气到不行,那天夜里提起锄头凶神恶煞地便赶往隔壁找人评理,那家人吓得赶忙澄清,半个字也不敢再提。
外婆生在富贵人家,只是家道中落,在她的那个年代,她自己也开过几家杂货店,因而尤其注重礼节,通透很多道理,也懂得很多人情世故。正如此,自我懂事起,她便教我为人处事的诸多道理,化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讲则是: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,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,如果我能宽恕人,体谅人——我都得感谢她。她教我出门在外,要和气讲理,要谦逊低调,但不能低声下气,要活有骨气。她教我要孝老爱亲,要以礼待人,但不能委屈自己,要活有自由。她只识字,没读过书,但她要我读,她老是说读书是最好的出路,她把我的奖状贴满在了她的房间。
可是有一天,外婆老了,日子明明是一天天过去的,外婆却仿佛是一日之间老去的。
老家的房子要翻新了,外婆要我们回家,在老房子里吃上最后一顿饭。照例是外婆掌勺,满满一桌,但却碗碗咸淡不知,碗碗不能下箸,外公忍不住念叨了一句,我看见外婆头上白发苍苍,眼里淌有泪花,从此往后,我再未见过外婆做这么一大桌菜了。
外婆老是犯腿病,父亲便带她去医院,留我一人看护。有好多次,我不敢相信我眼前病床上躺着的人竟是我的外婆。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她,我想到了那辆笨重的三轮车,想到了门前的高坡,想到了几年前在夕日里的朝我招手的身影,想到了太多,那些想到的种种日子,仿佛从她的手上开始爬,爬上了脸颊,爬上了额头,爬上了发梢,他们停在外婆的身体里不再出来了,他们化作痕迹,他们叫作岁月。回去的路上,外婆坐在车的后座,双手紧紧地握住车窗上的把手,呆滞地望向这个空荡的城市。窗外霞光万里,洒在她的银发上,我看着记忆里坡下的三轮车与身影渐渐随霞光远去,一言不发。
老家的房子终于翻新了,当我再一次回到这儿时,他们已经填平了陡坡,他们已经砍走了香樟,他们在新房门前开出一片空旷的庭院。我看见落日第一次毫无遮挡地撒入这个房庭,我只觉得陌生。一切都是新的,一切都显得熠熠生辉,可只有新而已,在这里,一切也都跟着远去了,我逐渐哽咽,再也说不出话了。
回神过来,我已经不自觉地走出了门,在这个大西北的天空下,我擎出手指,学着当初拖住白昼与黑夜的样子,这次却再也没能拉住白天,也没能够再等来谁。天空如常披拂上黑夜,我又失去了一天。我开始思索生命既然开始,为何要有尽头?倘若生命没有轮回一说,那么一个生命的离开,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永远逝去了,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惊悸。你我总该独自离开这个世上,这一生的日子就像一个掷入湖水的石子,水波荡漾后,终将沉寂,无人例外。那我们终将的逝去生命究竟又有何意义?
我站立许久,终于给出了我的一个答案。
生命会孕育新的生命,那些老去的生命在他历经完他都一生后,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新的生命的一生,我把这种影响,称之为延续。每一个孩子是这个家族生命的延续,是这个世界生命的延续。外婆教会我的一切,会影响我的一生,这种影响将化作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我一起活着。我会遇到新的人,有新的经历,而那些经历也会作为我的一部分与我一同活下去。这种一代代的延续,放眼古今上下,便交织成了民族。这么说来,我们生命中每一次触动,都将会是数百年前某一曾鲜活生命的回响。
是的,外婆并未老去,她在我心里,与我一起活着,永远鲜活,永远年轻。她所教会我的一切,使得日后的我对种种事情的种种看法,都将会有她的影响,我的后辈也会如此这般,这是生命的延续,生命的逝去并非毫无意义。
老白杨会再发新芽,外婆也从未老去,生命的歌将进行到底。